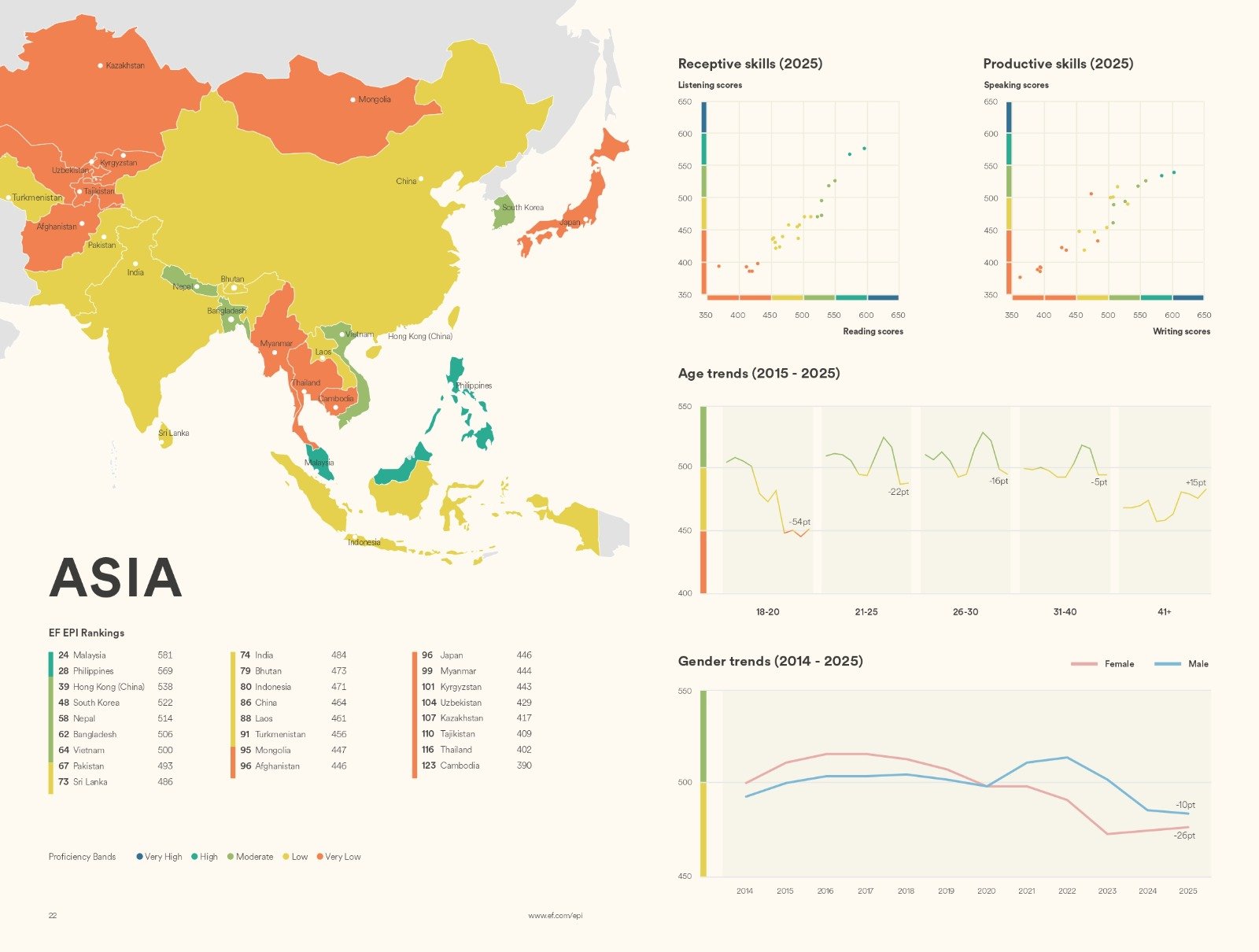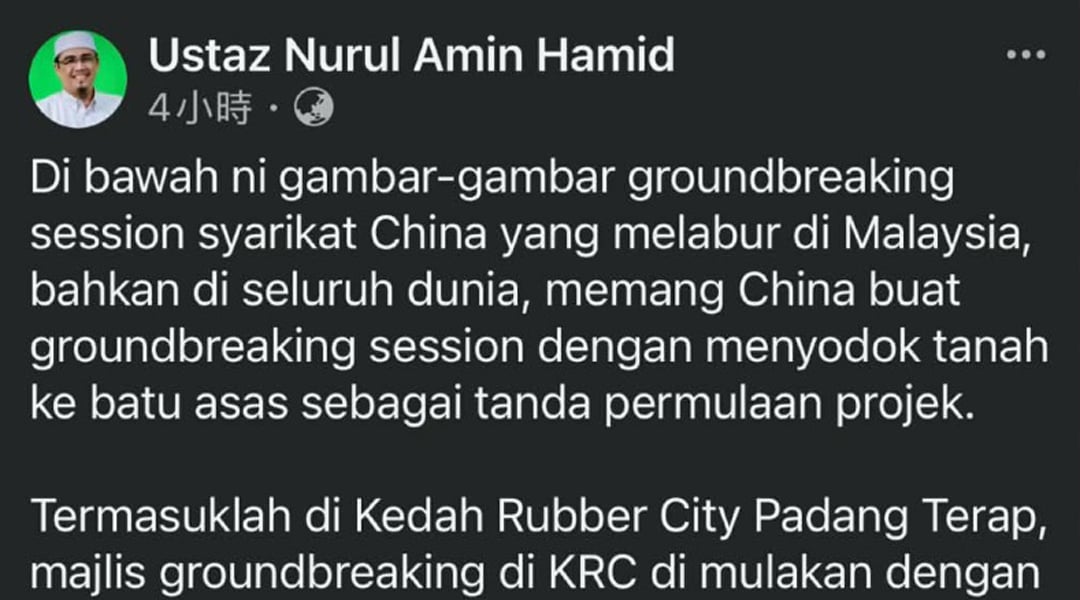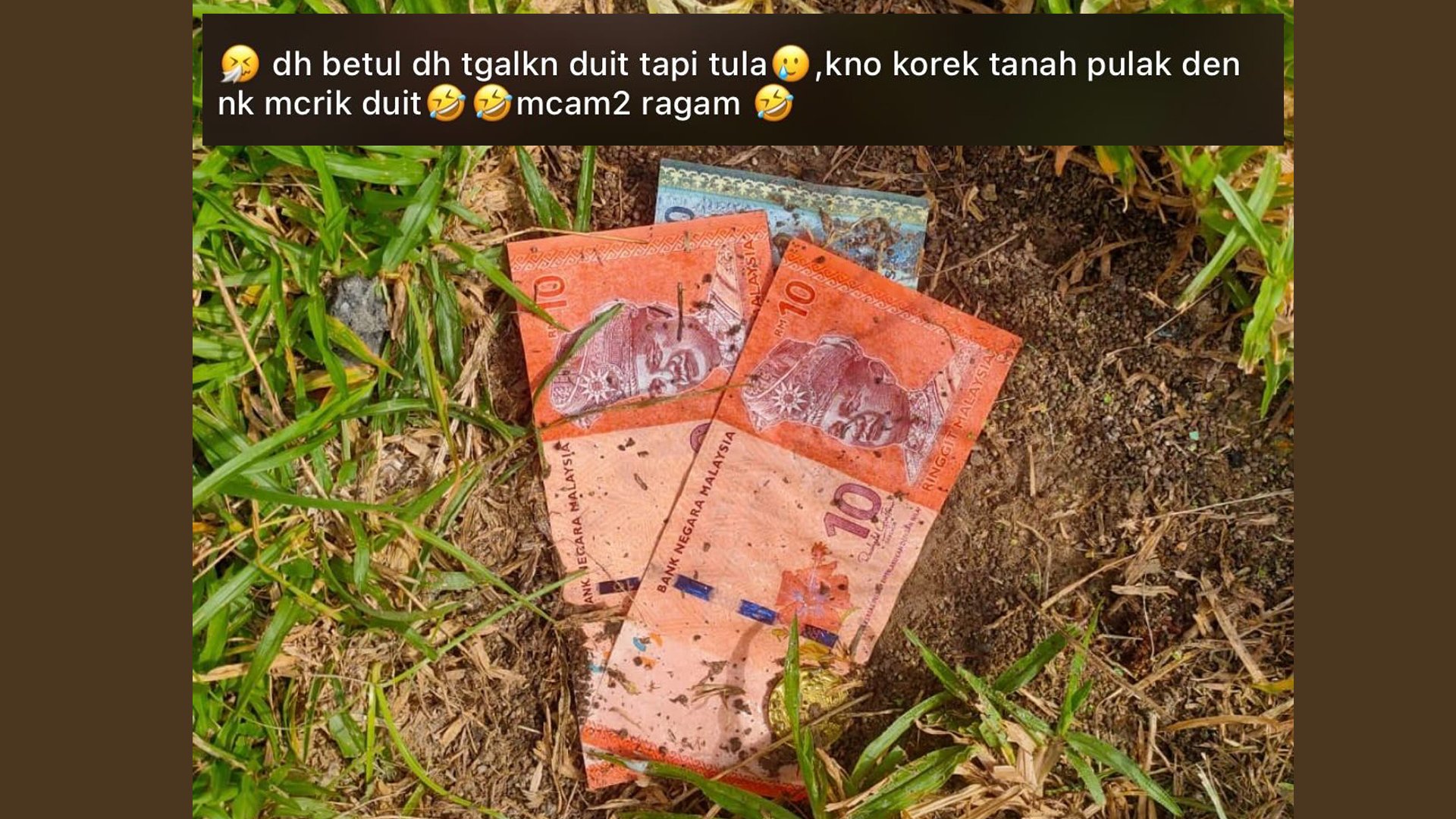文:陈晓云;图:受访者提供
当全球暖化越演越烈、极端气候频发,连空气、水源与食物这三大生存命脉都逐渐失衡、枯竭时,我们赖以栖身的地球正走向反噬人类的边缘。即便工程科技或AI技术再先进,也无法重建一个同样的地球生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非政府环保组织(NGO)如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肩负起捍卫环境正义与地球和平的使命。而在本地,槟州绿色机构(Penang Green Council)第一任总经理邓晓璇,即便卸下公职,仍以孤勇者姿态继续在各平台宣导环保理念,坚持守护这片土地。
不管你是在打着《王者荣耀》,拍着 TikTok,还是追看《经典歌曲比赛》;不管你开的是特斯拉还是Axia;不管你属于Z世代,还是上世纪的人——赖以生存的条件始终不变:空气、水源与食物。当自然因人类的发展而遭破坏,环境的珍贵资源也随之失衡。

环境教育与传播工作者邓晓璇指出,如果继续允许森林被砍伐,受影响的不只是原住民,我们所有人都难以幸免。
截至目前,人类能最明显感受到的环境失衡现象,当属气候暖化。简单来说,气候暖化是地球变得越来越热的现象。这是因为空气中累积了越来越多导致升温的温室气体,而能吸收二氧化碳、调节气温的森林却越来越少,全球气温因此持续上升。
频繁的工业活动、过度的个人交通出勤、空调使用等仰赖石油能源的人类行为,正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导致人为气候变化(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并恶化全球暖化。
槟州绿色机构第一任总经理、“与地球一起呼吸 SHUEN SUSTAIN”小红书专页创办人、环境教育与传播工作者邓晓璇指出,地球各个角落都无法幸免于气候暖化,只是受影响的程度与形式各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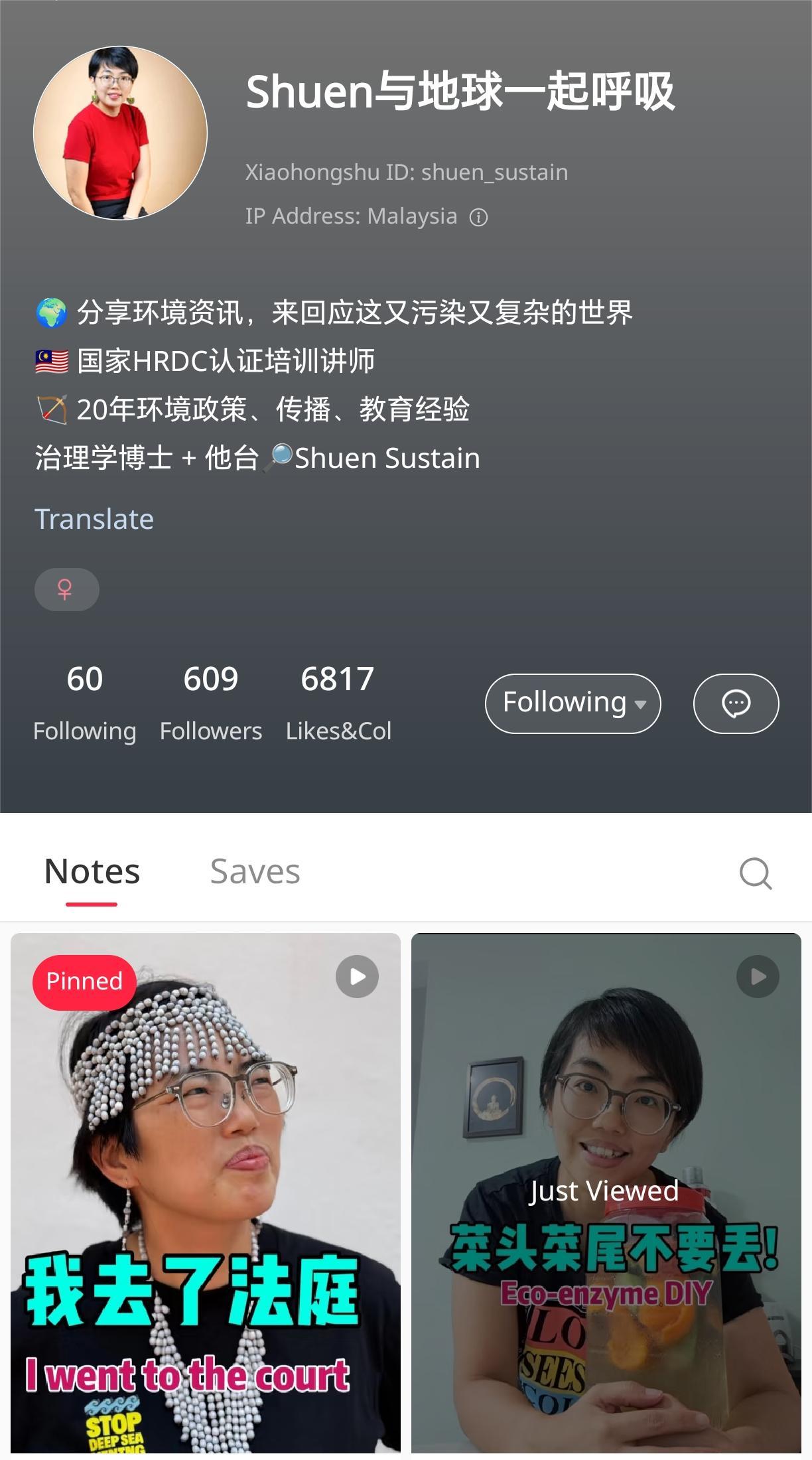
她举例,有些地方变得更寒冷;原本下雪的地方不再下雪,不曾下雪的反而开始下雪。而在马来西亚,气候暖化带来的后果则是极端降雨量的出现——一天内下了半年甚至全年的雨量,风调雨顺的气候已成过去。
“气候暖化也造成一些地区的冬季、旱季或雨季延长,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植物与农作物的生长。有些作物因此欠收,或质量下降。毕竟植物生长依赖当地的光照、温度、水份与土壤性质。”
她以我国金马仑为例指出,如今气温已不像过去那样低,直接影响农作物的种类与收成。“只要任何一个因素出现变化,都会影响粮食供应。若持续下去,有一天连水稻也无法收成,粮食危机便指日可待。”
令人忧心的是,在物资丰裕、食物垂手可得的现代社会,许多人明知气候暖化可能引发粮食危机,仍觉得事不关己——除了农夫。
“从历史可见,粮食危机曾是引发社会不公与动荡的主因之一,甚至导致战争。我们必须警惕,并以全人类的醒觉与行动,从源头上防止这种不公。”
她也补充,气候暖化可能带来未知疾病。科学家警告,冰山融化释放了封存在冰层数百万年的病菌,这些“获释”的病原体可能随洋流及全球航班传播,无人能置身事外。
若继续允许砍伐森林,后果可想而知。她反问:“你能想象直落巴巷国家公园被开发吗?能接受槟城街边行道树被砍光的景象吗?”
当街道树被砍,我们都会觉得更热,更遑论整片森林的消失——它必然改变整个气候模式。
此外,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马来半岛111 个市镇因此面临严重水灾,造成财物损失甚至人命伤亡。她提醒:“我们不能再说气候变化与己无关。”
“更何况,我们现有的基础设施是依据几十年前的气候状况设计的,虽然规划可用百年,但当时的地球还未出现如今的极端气候,这些设施已不堪负荷。”

只要一天人类还在世上,
气候就会持续暖化?
环境教育与传播工作者邓晓璇指出,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会议(COP)引用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IPCC AR6, 2021),即使人类立即停止所有工业活动和温室气体排放,全球气温仍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上升,因为地球气候系统不会马上冷却。
在新冠疫情造成全球经济大停摆的那三年,全球温度仍持续上升,但速度略缓,空气也明显变得清新。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指出,那段时间的碳排放减少只是暂时性的,之后排放量迅速恢复,温室气体浓度仍创下新高。
虽然减少碳排放不会立刻让气温下降,但持续努力终会开花结果。
“买东西”
也可以是气候行动
改善气候暖化必须从消费与生产两方面着手。邓晓璇说:“全球人口已达80亿,消费与生产模式不能再沿用人口50亿时的方式。”
她举例:“马来西亚如今有逾3千万人口,但思维与生活方式仍停留在1千万人时代。若每人每天丢一支吸管,那就是3千万支吸管,对环境的冲击可想而知。”
疫情后,一次性塑料使用量更剧增,加重了环境负担。她呼吁,若大家购买饮料时一致拒用吸管,就能每天减少3千万支塑料垃圾。
“我们的每一块钱都是一张选票。每个消费行为都在投票——投给我们想要的未来。既然知道塑料垃圾造成全球污染,为什么还用金钱支持它?这就是‘蝴蝶效应’,一个微小的改变能带来连锁反应。”

大改变需要
与执政者一起努力
气候治理中有个词汇叫B.A.U(Business As Usual)——意即“一切照常”。邓晓璇强调,在气候危机面前,我们不能再照旧处理,而要以“危机思维”应对。
“气候变化是全球课题,必须由各国政府共同承担。虽然像马来西亚这样的中小型国家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有限,但我们却是受害者,有责任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减碳责任与赔偿义务。”
此外,具有规模的环保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也经常与政府和政治人物对话,推动政策行动。
她指出,环境问题若要真正改善,除了靠个人行动,也需制度性的改革与政治推动。“有选举的国家,制度改变必须透过政治改革实现。环保组织的宣传目标,就是唤醒拥有投票权的一群,让他们理解环境议题的重要性。”
“我相信,怎么样的人民,就选出怎么样的政府。如果你只关心福利金,政府就只会给福利金;如果你不关心环境,议员也不会关心环境。”

狠角色
保护环境的组织往往被误解为“极端份子”。毕业于重庆西南大学治理学博士的邓晓璇说,她把环境工作视为一个“绿色光谱”,从白到深绿,而环保组织通常处于“深绿色”位置,因为主流发展观念太偏白,“我们只是试图恢复平衡而已”。
“有人觉得环保份子动辄反对发展,这其实不合逻辑——难道我们不需要呼吸或喝水?为什么发展一定要砍伐森林?森林是碳库,也能保护气候啊!”
她补充,一些环保组织设有科研部门,评估各国环境不正义问题,关注发达国家、政府或企业的决策是否损害弱势群体的环境与健康权。
她举例:吉隆坡万挠(Rawang Batu Arang)拟建垃圾焚化炉,处理多个县的垃圾,但当地居民被迫承受污染,这就是环境不正义。
继续砍伐森林,首当其冲受害的是原住民,他们失去干净水源、失去森林资源,陷入生存危机,却鲜少获得关注。“选票政治往往忽略原住民。”
不同于社会正义仅关注“这一代”,环境正义更关乎“下一代”。她反思:“比如核能发电,辐射废料由下一代承担;而当下一代出事,原告早已长眠。我们连公交电梯都常坏,如今真有条件建核电厂吗?”
邓晓璇理解人们想保护眼前的拥有,但提醒大家反思自身行为的长期影响:“当你能多考虑别人时,和平才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