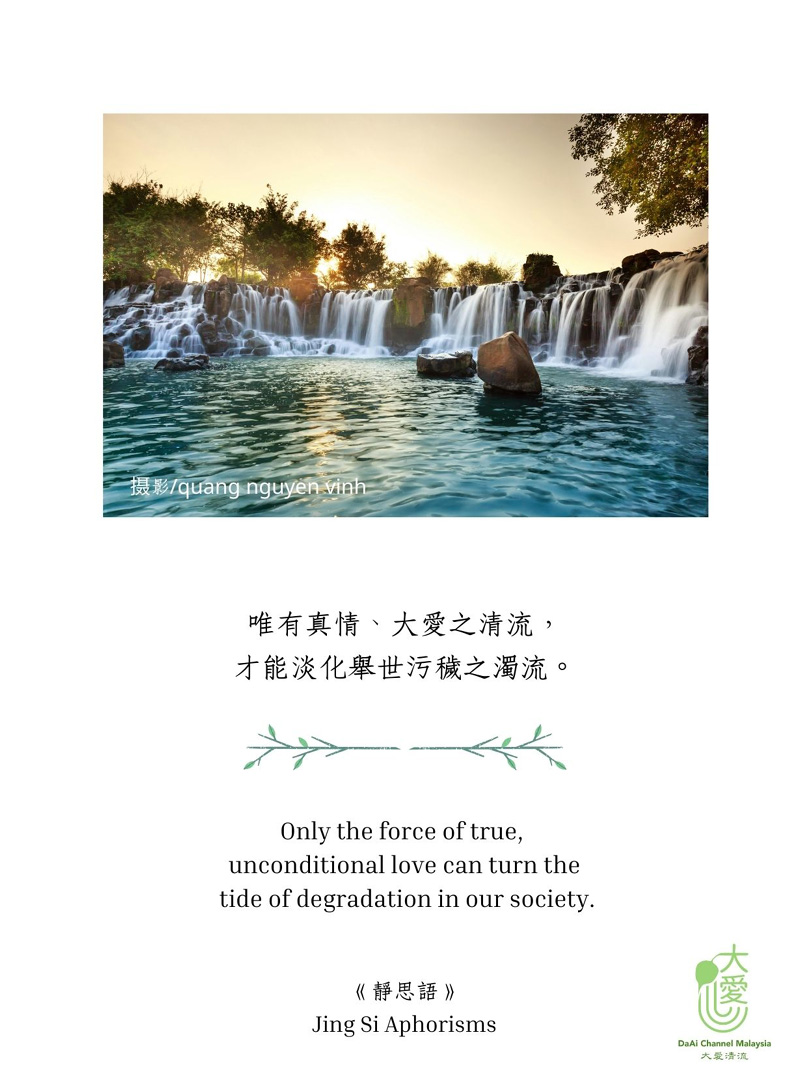文:郑文辉
就在新年期间打开报纸,看到一则报道说:柔佛苏丹依布拉欣指出,柔佛华社是柔佛州经济的支柱,他们的坚韧和勤劳必须受到认可。这是苏丹接受《星报》访问时说的。
他说:“请不要再说华人是外来者。他们帮助我们发展经济,然后称为马来西亚人,就如其他马来西亚人一样。他们是柔佛州子民,与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无异”。
——这是苏丹的开明,了解历史、又有清晰的远见;他能回看过去而瞻望未来。他的这个高瞻远瞩能让其他的政治领袖、政府人员及部门负责人能有所接受与反思,应该抛弃那狭隘的偏见和思想。认真思考问题,则是人民、社会、国家幸甚!
据历史记载,在明朝以来已经有华人来到柔佛,天猛公达因依布拉欣于1884年邀请华人在柔佛种植甘蜜和胡椒。苏丹依布拉欣还说,他的祖先也率先推出“港主制度”,进入柔佛的华人获得“港契”(Surat Sungai)的准证,在当地获得农耕种植活动。事实上,柔佛州就是在港主制度下开发的。
我出生的地方;麻河北岸的玉射小镇,就是于1883年在“港主制度”下开辟,种植胡椒、甘蜜而后发展起来的。
因此,我在这里是要谈一下早期的柔佛与中国的交往与港主制度的开发柔佛的情况。
历史上关于柔佛的最早记载,恐怕就是公元150年希腊地理学者佗利尔的《地理志》中曾提到南马的“巴冷达”港,其位置在今日柔佛河流域中。其次是在中国的载籍中出现,最早见于明时的《东西洋考》卷四说:“柔佛,一名乌丁礁林,男子削发徒跣,围慢佩刀,妇女蓄发椎结。王服与下无别,第带双刀耳。酋见王,弃刀于地,和南而立。各有尊卑位次,字用茭蔁,以刀刺之。……其酋好斗,屡开疆隙,彭亨丁机宜之间,迄无宁日。……
“物产:犀角、象牙、玳瑁、锡、片脑、蜡、嘉文蓆、木緜布、椒、燕窝、西国米、血竭、设药、梹榔、海菜、柿。”
“ 交易:柔佛地不产谷,土人时驾小舟载方物,走他国交易米,道蓬贾船,因此他处为市,亦有要之入彼国者,我舟至止,都有常输,贸易只在舟中,无复铺舍。”
在中国文献中最后一则的正式记载,为清《文献通考》卷二九七《柔佛条》中说:“柔佛在西南海中,背上而国,前临大海历海洋九千里达广东界,经七洲大洋到鲁万山,自虎门入口。国中无城郭,宫室王府即建于海滨,府治非砖瓦所成,支以竹木,蓋以茅叶。民皆环山而居,亦竹木茅叶为之。崇山峻岭,树木丛杂,野兽纵横。天时秋冬亦暖。王以柳叶为衣,左袵,下裳密缀小花为之,佩刀,首蓄发长二三寸,蒙以金花帕,跣足。民人冠用铜线为胎,幔以白布,衣短衫,或裸而以裳围其下体……饮食用手,忌猪肉,嗜烟。岁斋一月,举国绝食,见星乃食,历三十日始止。土产降香、乌木、西国米、冰片、海参、胡椒、燕窝之属。……”
我们从上述的二则中国史籍引文中,可以看出了早期柔佛的社会制度、民生、民情、风俗、物产以及商业贸易的一般情况。柔佛的早期虽然暧昧不清,但是,从上述的引文中可以看出与中国已有一定的交往。
在19世纪以前,柔佛不但人口稀少且地广荒芜。大约在1800年后,柔佛已种植胡椒和甘蜜,是当时的主要农作物,到了1830年至1850年代,柔佛竟是世界最大的甘蜜和胡椒产地。当阿武峇卡统治柔佛时,便成立了“港主制度”,这便开辟了全柔佛州的荒地。
根据历史的记载,在1850年第一位华人领袖开始住在柔佛后即获得授权书,即被委任为华人甲必丹,而黄亚福就是这样受聘来为苏丹在新加坡建王宫。去年9月,现在苏丹依布拉欣谕令恢复19世纪所颁布的“华人宗长”(Mejar China) 称号,委任新山开埠先贤黄亚福的后裔黄匡顺担任这个职位。而这次苏丹再强调:华人不是外来者,足见他的开明和有远见,这是柔佛州人民的骄傲,自豪与福祉。
我们回溯一下,当年在柔佛港主制度极盛时,土地得到充分的开发,而且几乎成为华人投资的事业之一。当时开港的都以潮州人为多,也有以公司名义办理的。那时全柔佛开辟一百多个港,我们还可以在地图上找到,但也不能齐全,据我所能知道的计有:德兴港、丰盛港、顺天港、永平港、义兴公司、张厝大港、永顺利港、余廷章新港、张厝子港、老东顺公司、和盛、黄厝、义和、加亨(臭港)、茂盛、合春、和兴、刘厝、老纪、洪厝、天吉、泽水、长发、周德、和信、新南、和丰、永丰、郑厝、陈厝、和平、新东、三合、沉香、永泰、和祥、成和、德顺、顺成、源发等。在麻坡属另有十三个港计为:头条、二条、玉射、芭莪、四条、嶺嘉、老厝、七条、哈蓬、老巫许、永兴、长发及新港。
于是,柔佛就在港主制度经营下,便发展繁荣起来了。然而盛极一时的柔佛州“港主制度”几乎已为人所遗忘了!我不厌其烦的把这老到掉了牙的旧事重提,希望大家不要忘了当初华人南来开荒种地居功不少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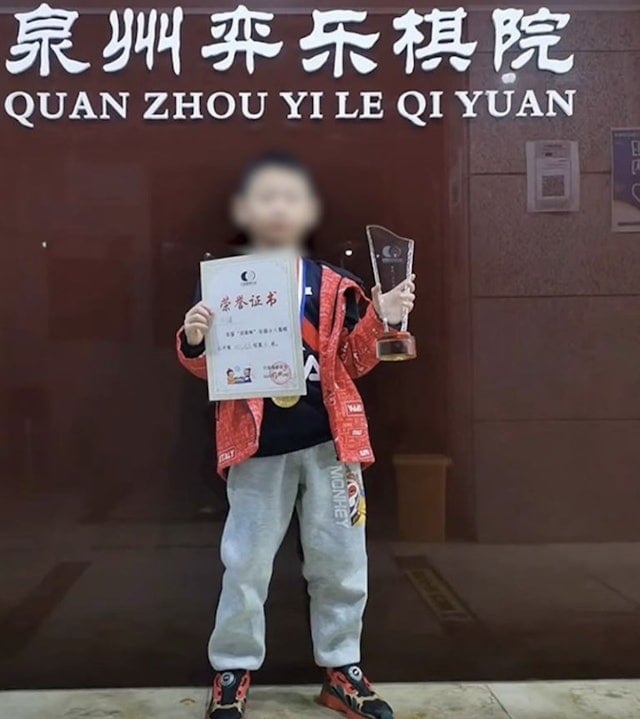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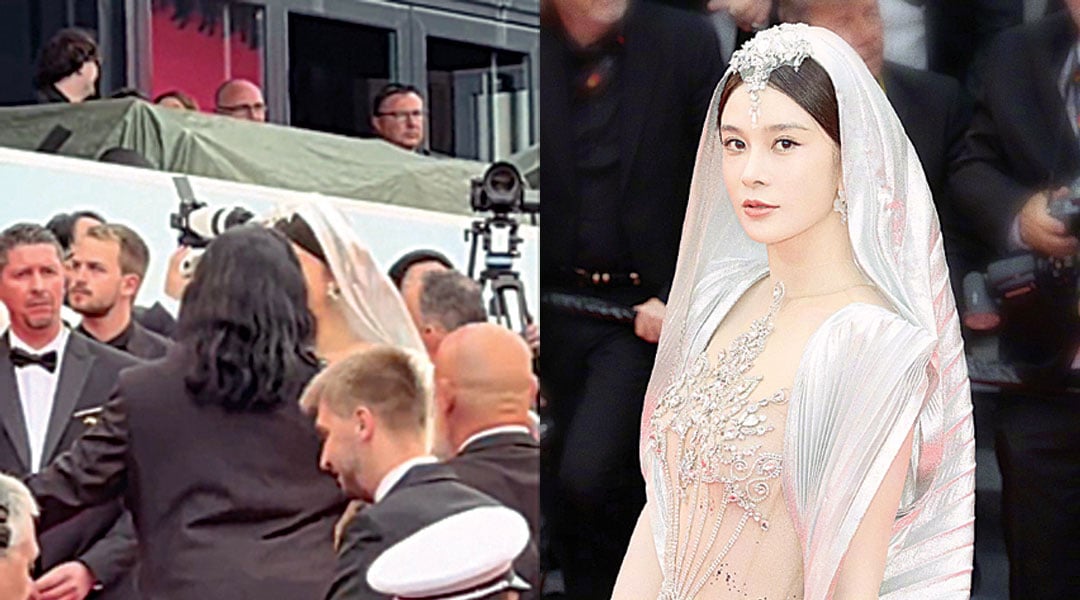




.jpg)